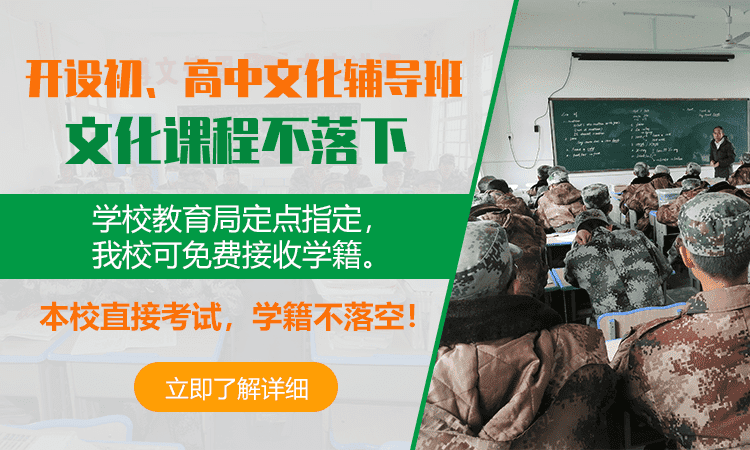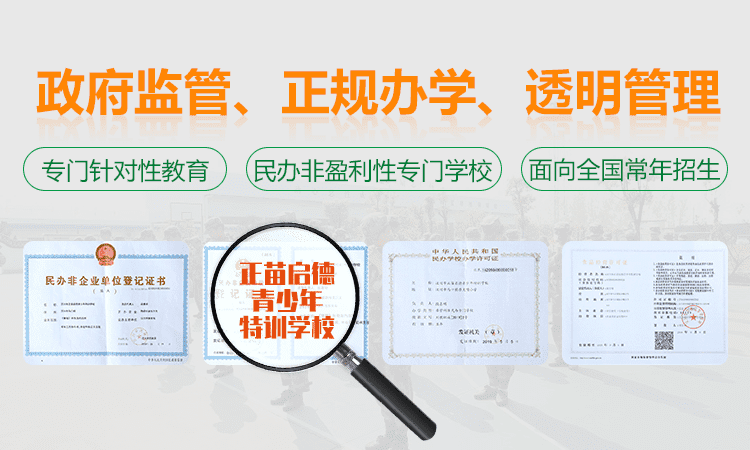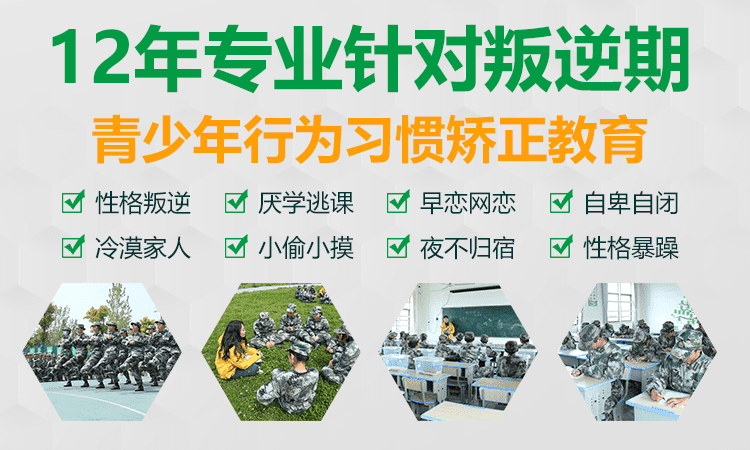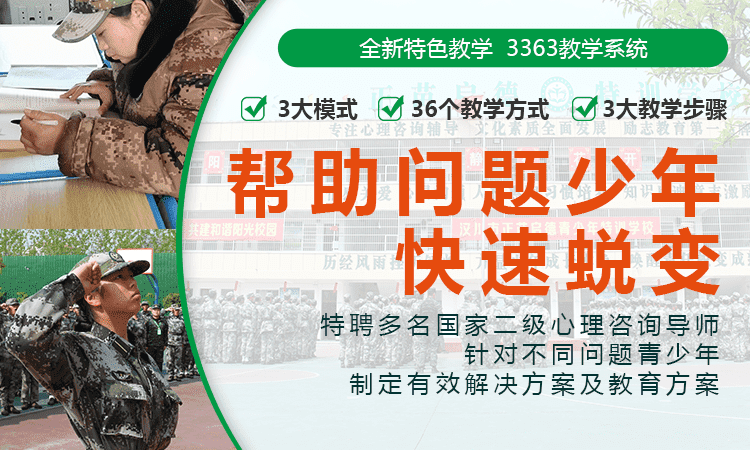世界各国针对青少年网瘾问题(中国有哪些治青少年网瘾的)
发布日期:2022-05-21 浏览次数:青少年网瘾怎么办?h2>网瘾是一个心理问题,网瘾是一种心理机制。青少年的自控能力普遍较差。为什么有些人沉迷于互联网,而大多数人不沉迷于互联网?成瘾者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吗?p>
趋利避害是一种心理机制p>
物流是现实世界的中心空间,虚拟世界是信息流中心的空间。这种区别,使得虚拟世界具有三大特征:实时性、仿真性和交互性。
人们具有生理、安全、交友、自尊、自我实现等需要,这些需要由低到高,低一层次的需要满足后,就会有较高层次的需要有待满足。绝大多数家长认为,为孩子们提供衣、食、住、行就足够了,忽视了孩子们还有着强烈的社会需要。患上网瘾的孩子,现实生活中难以满足其社会需要,但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虚拟世界里得到满足。
首先,由于仿真性,虚拟世界可以逼真地模拟现实生活,使人们在心理上获得同样的满足感。而且,这种满足还有着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种种优点。例如,在匿名的保护下,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不必承担任何后果,观点越是新、奇、特,得到的反响就越大、回应就越多,使得孩子们可以充分展现自我、实现自我。又如,网络自由平等的特性,为孩子们创造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新天地。再如,与现实世界相比较,这种满足是低成本的,仅仅需要付出一笔上网费。
其次,由于交互性,一个人可以同时与很多人,远隔重洋进行交流。尤其是平时比较内向、缺少关爱的孩子,深感孤独和无聊,在网上却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烦恼,充分满足其交友需要和自尊需要。如果遇到困难,会有很多人献计献策,使他们感受到现实生活中体会不到的温暖。
最后,由于实时性,人们可以在瞬间满足其社会需要,而在现实世界里,必须经历漫长的过程和耐心的等待。在游戏中,孩子们可以扮演各种角色,把握角色的命运,一夜之间就成为“盖世英雄”或“商界奇才”。很多孩子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经常遭到家长的斥责、老师和同学的蔑视。上网打游戏,不断“练功升级”,成为他们找回自尊、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
综上所述,网瘾问题的症结,在于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网瘾问题表面上来自虚拟世界,其根源却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互联网没有过错,患上网瘾的孩子也没有过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趋利避害、寻求快乐是人类为了保护自己、更好地适应环境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在这种意义上,患上网瘾的孩子是聪敏的、充满智慧的,他们知道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去表达自己的个人意愿,实现自己的个人追求。很多个案告诉我们,患上网瘾的孩子有着一些共同特点:专注、执着、有主见、接受新事物快、自我意识强。
虚拟世界的基本原则值得仿效
要解决网瘾问题,需要全社会通力协作。家长和老师的当务之急,不是简单地谴责网瘾,对孩子采取高压措施,而是要虚心向虚拟世界求教,彻底改造我们的教育体制,使得孩子们的社会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得到满足,不必去虚拟世界寻找替代物。虚拟世界的强大吸引力,来自一些值得仿效的基本原则:
(1)奖励原则。网络游戏可以通过升级和物品,对孩子们极其微小的进步予以奖励。现实生活中,哪怕是表现再差的学生,都有可能出现点滴进步,我们为什么不能及时予以肯定,以满足其自尊需要和成就需要?这些小的、微不足道的进步,将会逐步积累起来,渐渐成为习惯,形成良好的行为模式。
(2)娱乐原则。网络游戏以娱乐贯穿始终。在现实生活中,孩子们的学习过程为什么不能充斥着快乐?我们为什么不能重新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让求知过程洋溢着乐趣、充满着悬念?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学校开设各种兴趣小组,让所有孩子的好奇心都得到满足,潜能都得到发挥?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孩子们有一些主动性,有一些选择权,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得到更多的发展?我们为什么不能打破单一的分数标准,“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果做到了这些,我们就能让所有的孩子都充满自信,充满成就感,充分满足其社会需要。
(3)平等原则。网上的交流是平等的、自由的,这是上网聊天最吸引人的地方。家长和老师应该加强与孩子的交流,这种交流必须是平等的,不能进行简单说教,而且要用孩子的眼光看待现实世界,以过来人的身份,诉说青少年时期的艰难、烦恼和快乐之所在。
现在入学礼包等你来领
外国对青少年玩网络游戏采取什么措施?对青少年玩网络游戏有什么看法?
对于中国政府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而采取的措施,一些西方媒体炒作中国政府“专制”“钳制自由思想和文化”。《纽约时报》称,中国政府对网游的限制举措,反映出正加紧推动社会和企业“抛弃不健康的文化影响”。网络游戏区别与单机游戏而言的,是指玩家必须通过互联网连接来进行多人游戏。一般指由多名玩家通过计算机网络在虚拟的环境下对人物角色及场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操作以达到娱乐和互动目的的游戏产品集合。
但是,整体看所有群体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对每个青少年群体来说,几乎所有的心理健康指标都在恶化,而且这种情况在美国全国各地都存在。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每个种族的悲伤和绝望情绪都在上升。
1.社交媒体的使用
我认为,社交媒体不像老鼠药,对几乎所有人都有毒。它更像是酒精——一种轻度上瘾的物质,可以改善社交处境,但也可能导致少数使用者产生依赖和抑郁。
2.社交活动减少
心理学专家斯坦伯格强调,社交媒体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社交媒体本身,而是它所取代的活动。
斯坦伯格对我说:“我一直告诉家长,如果Instagram只是取代电视,我并不担心。”但现在的青少年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5个多小时,这个习惯似乎正在取代许多有益的活动。
从2007年到2019年,睡眠时间在8小时及以上的高中生比例下降了30%。与本世纪头10年的同龄人相比,今天的青少年与朋友一起出去、拿到驾照或参加青少年运动项目的可能性降低了。
疫情和学校关闭很可能加剧了青少年的孤独和悲伤情绪。哈佛教育学研究生院202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所有人的孤独感都上升了,但对年轻人来说增幅最大。
斯坦伯格说:“众所周知,密切的社会关系会减少青少年的压力。当孩子们无法到学校去见朋友、同学和老师时,这种社交隔离可能会导致悲伤和抑郁,尤其是对那些容易感到悲伤或抑郁的人。”
临床心理学家莉萨·达穆尔告诉我,没有哪种单一因素能解释青少年悲伤情绪的上升。但她认为,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世界压力越来越大。或者,至少,青少年对世界的认知似乎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过去10年里,对枪支暴力、气候变化和政治环境的担忧让青少年变得越来越紧张。”
对财务状况、气候变化和新冠大流行的恐惧、对获得社会认可和一定让自己成功的焦虑集合在了一起。
斯坦伯格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叠加效应。我们正走出疫情,然后俄罗斯突然开战。每天,感觉好像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带来对世界的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
不仅仅青少年有这种末日感,各种社交媒体渠道都在传递这种末日感。我们不能排除如下可能性,即青少年对世界感到悲伤不仅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令人悲伤的事情,而且因为年轻人随时随地都能接触到这些不断告诉他们应该对这个世界感到沮丧的网络信息。
4.现代育儿策略
过去40年里,美国父母——尤其是拥有学位的父母——花在辅导孩子、做专职司机和其他帮助孩子的活动上的时间增加了近一倍。
经济学家瓦莱丽·雷米称之为“幼儿竞争”。尤其是高收入父母,他们花更多的时间让孩子为能被有竞争力的录取做准备。我2019年采访雷米时,她对我说,她“无法相信我们的朋友为了让孩子上对他们施加了多大压力”。
“幼儿竞争”是一种上流社会的现象,不能解释青少年悲伤情绪的普遍上升。但这完全可以解释部分原因。
在2020年的《大西洋》月刊文章《美国的童年怎么了》中,凯特·朱利安描述了一个对家庭产生更广泛影响的现象:焦虑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远离风险和危险,无意中把焦虑转移到孩子身上。
朱利安强调了耶鲁儿童研究中心推出的一种名为“SPACE”的新疗法,即“针对焦虑儿童情绪的支持性育儿方式”。简单地说,这种疗法迫使父母不那么迁就孩子。如果女孩害怕狗,就鼓励她跟小狗玩耍。如果男孩讨厌蔬菜,就给他做焦糖西兰花。也就是说,在现代的育儿过程和孩子们的童年中,应用一点暴露疗法可能会帮助青少年更好应对一个复杂和充满压力的世界。
表面上,青少年的成长速度变慢;但在网上,他们的成长速度快得多。互联网不仅让青少年获得给予他们支持的友谊,还让他们接触到霸凌、威胁、有关心理健康的绝望对话以及一系列无法解决的全球问题——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的大集合。
搜索标签: